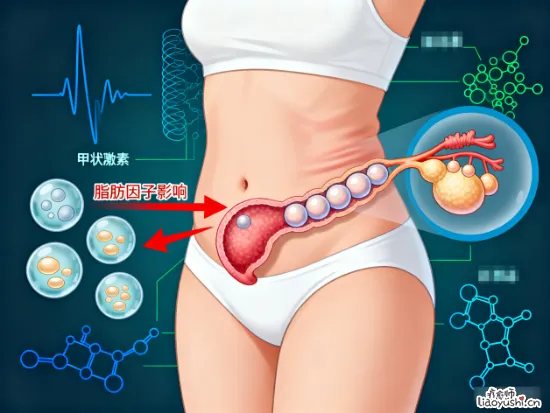那把美工刀第一次划破皮肤时,我竟然感觉到一丝轻松。血珠渗出来,密密麻麻的刺痛像蚂蚁在啃咬,但心里那块堵了十年的巨石好像裂开了一道缝。我缩在书桌下,听见客厅传来爸妈逗弟弟的笑声,尖锐又遥远。抽屉深处那个铁盒里,藏着我小学时得的七张三好学生奖状。它们曾经是我向父母兑换笑容的货币,现在成了废纸。
弟弟出生的那年我十岁。产房门口,我爸搓着手来回踱步,嘴角压不住地上扬。你马上要当姐姐了,以后要懂事点。他突然转头对我说,语气像在宣读圣旨。我捏着给妈妈折的千纸鹤,手心全是汗。那个粉红色的婴儿被抱出来时,全家呼啦一下围上去,姑姑的苹果滚到我脚边都没人注意。
最初我也试着当个好姐姐。半夜弟弟哭闹,我主动跑去冲奶粉,妈妈却皱着眉夺过奶瓶:水太烫了,你想烫死他吗?她眼下的乌青像两团墨迹,再没像从前那样摸摸我的头说宝贝真乖。
餐桌渐渐成了战场。弟弟把胡萝卜甩到我裙子上,妈妈抽张纸随意一抹:他小不懂事,你让着点。去年生日那条白裙子,现在晕开一片洗不掉的黄渍。爸爸下班带回一盒草莓,我刚拿起一颗,弟弟就蹬着腿尖叫,妈妈立刻把整盒推过去:弟弟爱吃,姐姐明天给你买香蕉。那个明天至今没来。
初二期中考试我拿了年级第一,家长会后班主任特意留爸妈谈话。这孩子是考重点的苗子啊!老师很激动。回家路上爸爸却一直叹气:可惜是个女娃,读再好也是别人家的。车窗外霓虹灯闪过他疲惫的侧脸,我攥着成绩单,纸张边缘割得掌心生疼。
家里到处是雷区。弟弟摔碎我的陶瓷存钱罐,那是奶奶临终前给的礼物,我妈扫着碎片念叨:罐子放那么高干嘛?弟弟才五岁懂什么。我缩在床角咬自己手腕,齿痕陷进皮肉里的时候,脑子里闪过班主任惊讶的眼睛:你手臂怎么青一块紫一块?
书桌成了最后的堡垒。直到那天弟弟把我的画册撕了折飞机,我失控地推了他一把。他后脑勺磕在茶几上哇哇大哭,我爸的皮带抽下来时带着风声:毒蛇!养不熟的白眼狼!血从嘴角流进衣领,我竟在血腥味里尝到解脱。那些画册碎片像雪片散在地上,其中一张是去年画的全家福,现在被踩了个鞋印。
第一次自残是在体育课后。同桌指着我的旧运动鞋笑:这牌子我奶奶都不穿。回家看见弟弟脚上崭新的限量版球鞋,我反锁浴室用修眉刀在腿上划。疼痛炸开的瞬间,同桌的讥笑和爸妈的责骂突然静音了。原来疼是可以开关情绪的闸门。

伤痕很快蔓延到大腿内侧。有次游泳课换衣服被闺蜜看见,她倒抽冷气:你疯了吗?我笑着撒谎说被野猫抓的。那天晚上她发来十几条消息,最后一句是:下周我爸妈出差,你来我家住吧。黑暗中手机屏幕的光刺得眼睛发酸,原来世上还有人看得见我。
心理咨询师林老师的办公室有盆绿萝。第三次咨询时,我讲到弟弟周岁宴那天自己发烧到39度,爸妈却带着弟弟去拍纪念照。他们忘了我还在家。我说得平静,手指却把纸巾撕成碎末。林老师轻轻推来纸巾盒:那个被丢下的十岁女孩,现在需要你抱抱她。
桌面的OH卡散落着各种图案。林老师让我选代表家庭关系的三张卡。我抽到笼子、断剑和暴雨中的小鸟。小鸟是你,她指着卡片,暴雨是孤独,但翅膀还在。那张断剑卡被我偷偷带回家,夹在日记本里。
改变像蜗牛爬行。有次弟弟抢我耳机听儿歌,在他扯断线的前一秒,我破天荒地按住他胳膊:这是姐姐的东西。他愣住的表情像看见外星人。晚饭时弟弟告状,我妈罕见地没训我,只说:以后自己的东西收好。
报复性学习的夜晚,台灯烤得太阳穴发烫。收到重点高中录取通知那晚,爸妈开了瓶红酒庆祝。碰杯时爸爸的手突然落在我肩上:给弟弟做个榜样。他手掌的温度透过校服传来,那么陌生。我低头扒饭,眼泪掉进碗里。
上周整理旧物,在弟弟的奶粉罐后面发现了蒙尘的千纸鹤。它们挤在玻璃瓶里,翅膀上还带着我稚嫩的笔迹:祝妈妈平安。我抱着罐子走到客厅,爸妈正教弟弟拼乐高。暖黄灯光下,那个曾经让我窒息的空间居然透进一丝缝隙。
明天我去看心理医生。饭桌上突然响起的声音把自己都吓一跳。爸妈同时抬头,我妈筷子上的青菜掉进汤里。要…要妈陪你去吗?她问得小心翼翼。我摇摇头,把千纸鹤罐子推过去:这个给你们。
那把美工刀最终被我粘上胶布扔进垃圾桶的时候,粘胶沾了满手。真麻烦,但总比血容易洗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