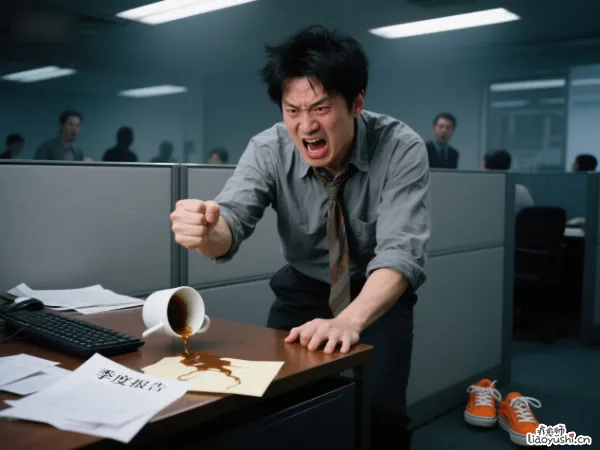煎饼被翻来覆去地摊在通州的街头,油渍溅到我的袖口上,那会儿是2011年,我18岁,刚把自考教材塞进煎饼车抽屉里。有个老顾客盯着我手上的《普通心理学》问:小妹看这干啥?能摊脆点不?书页被风吹得哗哗响,油星子正好落在马斯洛需求层次那章。是啊,煎饼要摊脆,人要活稳,可我的需求层次卡在生存线上动弹不得,十三岁辍学,父亲车祸去世,继母烧了我的奖状,头虱和地下室发霉的被子是青春期的全部记忆。
自考那四年,隔断房的墙板薄得像纸。隔壁情侣吵架声和我的英语磁带声打架:abandon,a-b-a-n-d-o-n…
房东大妈踹门吼:装啥文化人!
成绩单被拍到同事群里那天,群里死寂得可怕。不被看见的挣扎,比明刀明枪更磨人。后来才知道,那种持续坠落的无力感,心理学管它叫动机与愉悦维度缺损,听着真高级,我当时只会缩在网吧收银台后啃冷馒头。(突然想到个事儿啊,前两天看到个研究说双相患者对负面词反应比常人快0.3秒,难怪我当年背failure这词特别顺溜…)
转折点挺玄幻的。快递公司接投诉电话时,某个上海出租车司机在QQ对话框弹消息:自考看过没?
这五个字像根绳,把我从泥潭里往外拽。专科本科四十多门课,在公交车摇摇晃晃的扶手上背完了。可等到老公考上研究生,差距还是裂成鸿沟。考研失败那晚,深圳出租屋的麦当劳汉堡吃到反酸,月薪过万的喜悦被碾得稀碎。
香港理工的offer来的时候,雅思考场外的玉兰花正败。英语?你得理解一个连音标都不认识的人,把neural抄在煎饼包装纸上的日子。中介说要花一万写推荐信,我拍桌子:老子自己写!写推荐信的那个凌晨啊,文档里I am打成I an十七次,咖啡渍比申请理由还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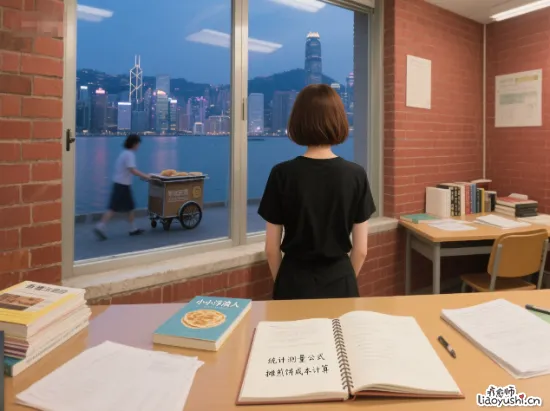
跑题了跑题了…
有个镜头总在脑子里闪:2009年父亲躺在ICU,我攥着他温热的手听医生讲肺破了。没哭,真的没哭。反倒是去年在芬兰做访问学者时,看到街头赶马车的老头,眼泪突然被决了堤。心理所论文说这叫延迟情绪释放,那些年没消化完的痛,总会在安全时翻涌。
双相诊断书是偷偷去拿的。医生指着快速循环型那行字解释:抑郁期像灌了铅,我噗嗤笑出声,这不就是我自考时瘫在床上的感觉吗?原来早和它交手多年。现在博士论文卡壳时,仍会整夜盯着天花板,但区别在于:我能摸着胸口对那片虚无说:看见你了,请坐。
在芬兰的雪地里采访抑郁症患者,金发姑娘突然问我:你怎么懂我们的绝望?
我转着咖啡杯笑:你知道煎饼鏊子多少度吗?200度。人把手放上去会起泡,可面糊能变成美味。
她眼睛倏地亮了。
陈楚侨研究员团队去年有个发现,说阴性症状其实藏着跨诊断密码。翻译成人话就是:甭管抑郁双相还是创伤应激,不被理解的孤独感才是公敌。
就像当年自考群里突然跳出的那句:姐妹,统计测量题怎么解?,看,微光就是这样接力的。
十四年从服务员到博士生的跨度常被说成逆袭,可真相是:我依然会在地铁坐过站,依然把中枢念成中区。区别在于,煎饼车抽屉里的自考书变成了博士论文,而当年那个躲在网吧幻想自己是大学生的女孩,终于走进了窗玻璃倒映的世界里。
(写到这里,窗外的维港灯光把键盘染成金色。跑个题啊,当年通州城管追我煎饼车时,可想不到这姑娘有天能在这里看海,命运这玩意,真的有意思。)
当玉兰花坠落在雅思准考证上,当隔断房里的英语磁带绞成乱麻,当煎饼鏊子烤烫了心理学笔记, 一个疯子终于学会, 把诊断书折成王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