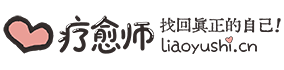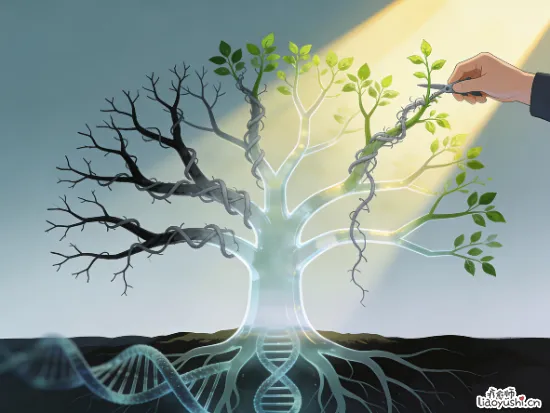那个状态啊,怎么说呢…像是胸口一直塞着块湿透的旧抹布,沉甸甸的,带着一股怎么都拧不干的霉味儿。日子被一种沉重的灰色给完全刷了一遍,连阳光都显得过分刺眼又虚假。醒来?醒来就是一种巨大的疲惫。该做的事,那堆事情不会消失,但…但力气被抽干了,真的被莫名其妙抽干了,仿佛有个看不见的阀门在身体里被谁拧紧了。动一下手指都觉得费力,站在那里,感觉整个人是悬空的,脚底下软绵绵的没什么真实感。脑子里那个嗡嗡的声音像是坏掉的收音机信号,断断续续,反复念叨着:有什么用啊……停下来吧……撑不下去了……
它们被不断播放着,循环着,像是怎么也拔不掉的劣质广告。
我甚至不记得是第几次,手指在书架上划过那些买回来堆着却没心思翻开的厚书了。《金刚经》那本薄薄的小册子,封面是那种很旧很旧的暗黄色,有点褪色了,边缘甚至有点卷。它好像被谁遗忘在那儿似的。
啊,对了,那天窗外的雨特别大,哗啦啦砸在玻璃上,邻居好像又在吵架,声音从雨声的缝隙里挤进来一点,模糊得很。大概就是这种无所逃遁的沉闷里吧,那本经书才被拿了起来。最初几页简直如同天书,不,比天书还令人烦躁。”如是我闻”,”须菩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些词句像是一群穿着怪异服装的陌生人,在我疲惫不堪的脑子里僵硬地列队游街,完全找不到入口。
太拗口了,真的太拗口了。思维被这些东西完全打乱了节奏,甚至还不如听窗外的雨滴声有规律。耐心被迅速地磨损着,磨损到了一个危险的临界点。算了,算了,看它干什么呢?不如睡一会儿?或者继续盯着天花板发呆?这两种念头在脑子里拉锯,但手还是没合上书页。也许是太无聊了,也许是别的什么说不清的倔强,视线还是在那古怪的文字上机械地移动着……
鬼使神差地,竟然又翻过去了十几页。那些绕口的名字和抽象的概念,还在顽固地挡着路。
我记得那天下午,光线有点暗,屋里闷得很。猫在我脚边蹭来蹭去,喵喵叫着要吃的,我都没力气理它。然后那句话,就这样毫无征兆地撞进了眼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
它被印刷在粗糙的纸张上,短促得似乎和其他密密麻麻的经书没什么两样。可就在那一刹那,脑子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咔哒”响了一下,像生锈的锁芯终于被钥匙拧动了第一圈。那个沉重的、压得我喘不过气的”我”,那个浸泡在无边无际痛苦里的”我”,那个感觉被整个世界抛弃了的”我”……它……它难道是被谁画出来的?被我自己画出来的?这个念头本身就很荒诞,带着一股凉气,咝咝地钻进心口的沉闷里。

念念不忘的,都是坏的东西。那些别人无意间说的一句话,一个眼神,工作里某个瞬间的错误,童年阴影里某个冰冷的角落……这些碎片被大脑这个过分勤劳又极其刻薄的工匠捡拾起来,一遍又一遍地打磨、抛光、放大,最终被镶嵌在意识宫殿最显眼的位置,日夜闪烁着令人心悸的寒光。我精心供养着它们,像供奉某种扭曲的神祇。它们是我的所有相。这些痛苦被如此真实地感受着,沉重到每一根骨头都在哀嚎。
可经书里那个单薄的词,虚妄?像针尖一样刺了一下。我那坚不可摧的痛苦堡垒,难道竟只是一座……沙雕?被潮水轻易带走的东西?这想法太挑战底线了,几乎带着某种亵渎感。沙雕?怎么可能?我的失眠是真的,胸口堵着是真的,流不出的眼泪也是真的!这怎么可能仅仅是被标记为虚妄呢?不对,这肯定不对。愤懑夹杂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恐慌冒了出来。
但那个念头像个固执的藤蔓,一旦找到缝隙,就开始顽强地缠绕。虚妄、非相,这些词带着一种奇怪的回响,在脑子里盘旋。它们搅得我坐立不安。
某天下午,那团湿抹布一样的沉重感又来了,死死地压在胸口。烦躁像一群毒蜂在嗡嗡乱撞。桌上正好摊着一张没用的打印废纸。几乎是出于一种泄愤的本能,我猛地抓起它,不是揉,是撕。刺啦!那声音异常清脆锐利,像是撕裂了什么沉闷的帷幕。纸张的纤维在指间反抗着,发出微弱的哀嚎,但还是被一股蛮力完全撕裂开来。接着是第二下,第三下……
虚妄!
刺啦!
非相!
刺啦!
碎纸片像被惊吓的白色蝴蝶,纷纷扬扬地落在地上、桌上、甚至我的衣服上。这个过程,带着一种原始而粗暴的快意。每一次纸张被撕开的破裂声,都像是一柄钝刀子,在笨拙地切割着捆绑在我心上的那些沉重绳索。每一次干脆的撕裂声响起,胸腔里那块冰冷坚硬的重物,似乎都被撬松了一点点。是错觉吗?也许是。但那短暂的、奇异的轻松感,是真实的。
看着满地的狼藉碎片,一个荒谬却又清晰的念头冒了出来:我紧紧抓住不放的那些痛苦,那些让我窒息的念头,它们本身,难道不也只是一张可以被撕碎的纸吗?它们被构建得如此庞大、如此真实,压得我喘不过气,但其本质,是否同样脆弱,同样可以被刺啦一声,完全分解?
它们是被精心建构起来的、耗费心力的巨大幻影。我一天一天地喂养它,用我的恐惧、自责、所有灰暗的念头去滋养它,直到它庞大到遮蔽了整个世界的光。而《金刚经》递过来的,是一双极度陌生的眼睛,让我看到,这怪兽狰狞的面目之下,不过是无数暂时聚合又注定离散的念头尘埃。痛苦本身,只是一个顽固的、被过分放大的念头汇合体罢了。它被我的执着一再加固,最终变成了囚禁自己的牢笼。
这种感觉…很难一下子说清。像什么呢?像你死死捏着一块烧红的炭,剧痛让你根本无法思考,只知道要捏紧,仿佛捏紧就是存在意义。而有人突然告诉你,快看,你捏着的其实是一团跳动的虚影。你半信半疑地松开一点指缝,咦?那灼烧感似乎减轻了?再松一点,灼痛竟然真的在减退……
当你最终完全摊开手掌,那所谓的炭块和它带来的酷刑,如同被风吹散的烟尘,消失得无影无踪。痛苦竟然就这样被自己放走了?原来它一直只是寄居在心灵褶皱里的幻影,被我们自己的固执和恐惧喂养得如此庞大狰狞罢了。
是的,我依然会碰到难熬的日子。那块湿抹布的沉重感偶尔还是会偷袭。但不一样了,真的不一样了。当熟悉的灰暗试图笼罩下来时,那个曾经让我惊愕的念头会像水底的浮木一样浮现:哦,又来了?这张破纸。学着做那个撕纸的人,不需要愤怒,只需要一点点觉察的清醒。
看到那个念头升起,认出它的本质,它便失去了压垮你的肯定重量。如同云遮住了太阳,但你知道云后面,光一直都在。那份沉重感再袭来时,心底反而有种奇异的笃定升起:哦,是你啊。这次,又能停留多久呢?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话啊,最初觉得玄之又玄,不过是些缥缈的句子罢了。但当你真正在撕碎那张纸的瞬间,感受着某种无形的沉重也随之崩解消散时,那些古老的文字才猛地扎进了血肉里,原来它们不是在描述某种高高在上的哲学命题,它们只是在指认我们自身那深陷其中、日夜挣扎的困境本质。那些看似坚固如山的痛苦,不过是一场我们太过投入的幻梦。醒来那一刻,世界仍是世界,而沉重的冰山,竟已化作了掌间微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