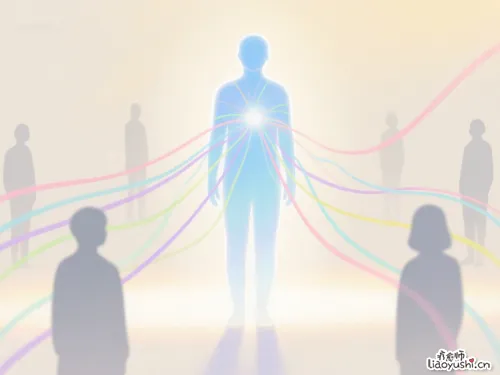上周二早上,我差点和地铁上踩我脚的人吵起来。那人连句抱歉都没有,还瞪我一眼。我胸口那股火啊,烧得我上午开会都在走神,键盘敲得噼里啪啦响。同事问我是不是早餐吃了炸药,你看,情绪这玩意儿,藏都藏不住,伤人又伤己。后来我跑到楼梯间,对着窗户做了个奇怪的事:问了自己三句话。十分钟后回工位,同事愣愣地说:你中彩票了?脸色忽然松了。
其实哪有什么彩票。我只是用了圣多纳释放法,一套美国人莱斯特·利文森在70年代搞出来的情绪卸载术。这人挺神的,据说死里逃生后顿悟了,发现所有痛苦都源于三个欲望:想要被认可、想要控制、想要安全。比如地铁上发火,表面是对方没素质,深层是我觉得被冒犯(求认可),想让他道歉(求控制),甚至担心鞋被踩坏(求安全)……呃,虽然那鞋也就两百块。
突然想到昨天咖啡洒衣服上我也暴怒过,啧,今天得再释放一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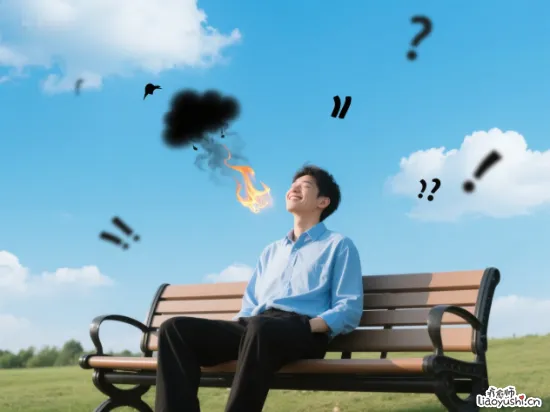
这方法的核心就俩字:放手。但不是硬压下去,而是像松开攥紧的拳头。
具体操作简单到像骗人,就反复问自己:
1我现在能放下这感觉吗?
(别思考能不能,直觉答能或不能都行)
2我愿意放下它吗?
(哪怕小声嘀咕不太想也算诚实)
3什么时候放?现在吗?
(通常问到这儿,身体会自己叹气)
我第一次试时嗤之以鼻。当时前任在朋友圈晒新欢,我酸得胃疼。抱着看你能多离谱的心态,瘫沙发上问这三句。第一遍答能放但不想放,第二遍愿意放可凭什么我放,第三遍……突然觉得没意思了。不是压抑,是像气球噗地漏了气,胸口那片锈铁般的沉重居然散了。后来再看他动态,竟然无感了,是真的无感,滑过去像看见广告牌。
当然也有卡壳的时候。比如老板把项目搞砸了却甩锅给我,我躲进厕所隔间狂问十遍能放吗,怒火依然噼啪炸。这时圣多纳的第五步管用了:释放想改变怒火的欲望。
说白了就是:我非要立刻平静吗?算了,气着也行。结果一松劲,愤怒自己溜了。这反逻辑的操作,像给野马卸了鞍。
为什么放手反而有用?
心理学说,情绪本质是能量。我们总习惯要么憋着(内伤),要么爆发(伤人),却忘了第三种本能:让它流走。有个比喻特形象:情绪像高压锅里的蒸汽,放气阀一转,危险就消解了。圣多纳法就是拧阀门的手,不解决具体问题,但卸掉情绪污染,脑子自然清明。
有个重度拖延的朋友靠它写完了论文,她说:不是突然勤奋了,是不想写的焦躁释放后,身体自动坐到了书桌前。
不过别期待秒变圣人。我试过对楼上深夜跳绳的邻居用这招,头三天照样咬牙切齿。但持续释放求他安静的欲望后,居然能边听跺脚声边睡……后来甚至给他送了耳塞(他脸红收下了)。你看,释放不是忍让,是把能量收回来养自己。
也有质疑声。有人说这是情绪逃避,该闻的垃圾偏要直接扔。但我觉得,当愤怒像烈火燎原时,先灭火再谈反思,总比烧成废墟强。就像莱斯特说的:你不需要嗅垃圾才知道它是垃圾。
坚持半年后,我变了点。遇到糟心事,身体会自动吸气问:能放吗?,像条件反射。变化是细微的:以前客户刁难我能气三天,现在嘟囔一句随你吧就翻篇;过去失恋沉溺痛苦,如今哭两晚后胃突然咕噜叫:饿死了,吃碗面去!痛苦还在,但我不再是粘蝇纸,而是流水了。
最后划重点:
1、别等情绪够大才释放,细微烦躁时就练手,麻木感也能放;
2、重复是钥匙,一组问题没清空就多轮轰炸,像拆洋葱;
3、决定放手本身就是行动,哪怕你根本感觉不到变化。
圣多纳法不是魔法棒。该吵的架可能还得吵,该疼的心依然会疼。但它像给心里装了个排水阀,洪流过后,土壤还在,还能种新的花。就像此刻我打下这行字时,楼上邻居又在跳绳。但奇怪,我听着那哒哒声,居然觉得像雨打芭蕉。
要不…给他再送盘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