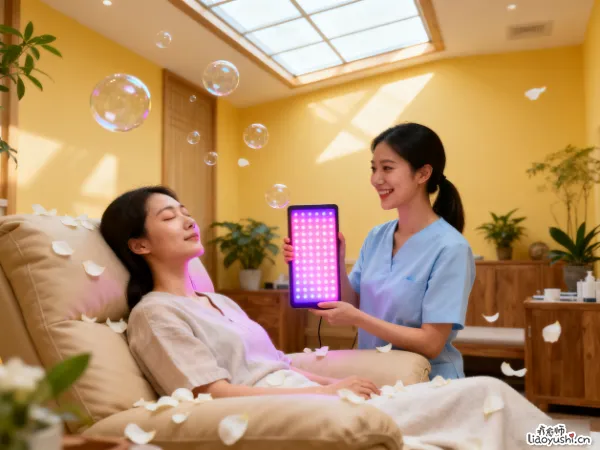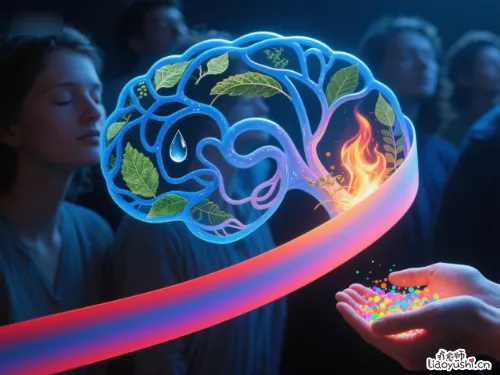那天下午我盯着电脑屏幕,胸口像塞了一团浸了水的棉花。你知道那种感觉吧?明明没发生什么大事,但就是喘不上气。同事在群里发了个笑话,所有人都在刷哈哈,我也跟着打了个表情。手指头是冷的。
后来我抓起手边小孩的图画本,还有那支快没水的紫色彩铅。本子角落画着只歪歪扭扭的恐龙。我就在空白处开始画圈。一圈,两圈…力道有点重,纸都快划破了。画着画着,那些圈变成了乱麻,又变成一片乌云状的黑疙瘩。根本没过脑子,就是手腕自己在动。
原来这叫把潜意识视觉化。书里说得太玄乎了。其实简单说就是,你心里堵着的东西,靠嘴讲不出来,手却能替你扔到纸上去。(对了,冰箱里那盒酸奶快过期了吧?等下得去吃掉。)

以前我总以为得画朵花、画棵树才算画画。后来看心理老师示范,她直接拿马克笔往白板上砸红点。这是上周三我开会时的怒火,她说。那些点像血渍一样溅开。我一下子被击中了。情绪不需要被美化,它只需要被看见。
有人把情绪分成七种颜色。红色是炸开的鞭炮,橙色像晒进被子的阳光,蓝色是沉到海底的秤砣……我那天涂的黑疙瘩算什么?大概是蓝黑墨水混了铁锈吧。但奇怪的是,当那片污渍在纸上成型时,喉咙里那团棉花好像松了一点点。
为什么非得是画? 和写日记不一样。写字还得组织语言,而情绪经常是哑巴。有个姑娘叫小华,她被学业压得发抖,却只会说我没事。心理师让她画恐惧,她画出纠缠的荆棘和下沉的巨石。石头坠落的线条,比一百句我压力大更有力。
和聊天也不一样。有些委屈说出来就变形了。但当我同事上周把她的焦虑涂鸦给我看,整张纸爬满蜈蚣脚似的短线条,我后背立刻泛起鸡皮疙瘩。对!就是这种随时要断掉的感觉!我们都松了口气。有些心情还没名字,但一条线就能让它现形。
科学说法是,涂抹动作能绕过理性审查,把右脑仓库里的情绪渣滓掏出来。左手画混乱的波浪,右手画尖锐的三角,据说是在激活不同脑区对话。但我只觉得,当紫色铅笔唰唰划过糙纸时,耳朵里嗡嗡的杂音被这摩擦声盖住了。
画画时的身体是被驯服的。呼吸不知不觉变深了,铅笔屑在阳光里打转,窗外快递车倒车请注意的电子音忽近忽远。这种状态他们称之为心流,而我管它叫暂时把烦恼调成静音。
当然不是非得画得多艺术。在青岛理工那场情绪自救实验里,学生在情绪转换器站点疯狂涂鸦:有人画流泪的太阳,有人把纸抠出破洞,还有人只反复描一个忍字。最震撼的是一张全黑的画,作者在旁边写:涂黑第三层时,我哭出来了。(纸巾盒该补货了……这种日常琐事反而让人踏实。)
现在我桌角常备一叠打印废纸。焦虑时画火焰,画完就揉成团投篮似的丢进垃圾桶;憋屈时用红笔戳满纸的小点,像给隐形的敌人扎针;如果画出一朵花瓣歪扭的花,哪怕下面接着监狱般的铁栏杆,我会给那朵花描上金边。这是属于我的情绪创可贴。
最近一次崩溃是深夜改方案。光标在屏幕上鬼打墙似的跳,我忽然抓起橙色荧光笔,在便利贴上画了个龇牙喷火的霸王龙。把它贴在显示器边框上。看着它气鼓鼓的样子,我居然笑出声。你看,情绪被命名的那一刻,它就丧失了一半的杀伤力。
所以下次胸口发闷时别急着刷手机。随便抓张收据、外卖单,画一道闪电,或者涂个湿漉漉的蓝圈。不必让人看懂,更不必解释。 那些线条是你的秘密,也是你的出口。
当颜料在纸上漫游时,没有评判的眼睛,没有催促的秒针,只有你自己在说:原来藏在这里的礁石,终于浮出了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