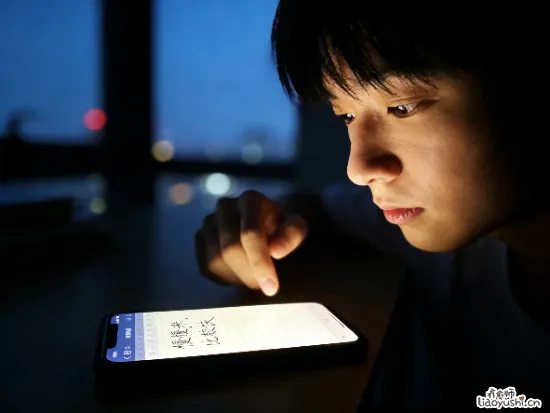我坐在那张被无数人坐过、磨得有点发亮的公园长椅上,靠着硬硬的椅背。耳朵里灌进来的,是树上那么热的天里还在拼命叫唤的知了声音,简直像灶上油炸一样的声响,但这嘈杂还是盖不住旁边那对夫妻的声音。
女的在吼叫,每一声都如同爆炒栗子般突然炸裂:跟你说了八百遍了!走路看看周围!差点撞到孩子没看见吗?
男人的声音则相反,像一块被水浸泡软化了的饼,慢悠悠飘过来:看到了看到了,我不是… 没撞上嘛…
音量小得几乎要淹没进空气里。
听着听着,我忍不住觉得有意思起来,这火爆的急脾气和温吞水性子,怎么能凑到一块儿去的?这根本就是冰与火在一口锅里煮啊!可奇妙的是,他们吵归吵,那男人手臂却始终没松开女人肩膀,女人骂着骂着,声音里的火味也渐渐化了冻。
静下来想想,嘿,我们很多时候啊,总在找那个所谓的完美另一半,要温柔体贴,要懂我心思,要上进还得顾家。可现实常常是,那个被你选中、或者选择了你的人,那些一开始让你心痒心动的地方,日子过久了,反倒成了你最想把他按进沙发里揍一顿的毛病。
你爱他说话风趣,后来却发现他这张嘴在正经事上能把人气得冒烟;你当初爱上她整洁有序的魅力,后来却被她追着你捡袜子的脚步声烦得想逃离。我们心头描绘的那个完美影子,到底是被谁刻上去的啊?是谁规定了好伴侣就只能是那一副模样?

说到牙刷,我小时候用的还是猪鬃毛做的呢,硬邦邦的,刷得牙龈出血。现在嘛,科技发达了。但我们心里那个完美伴侣的形象,好像还停留在猪鬃毛牙刷的时代?固执地觉得只有那一种标准答案才配得上自己。
真的。我是说,有没有可能,那个让你跳脚、让你无奈、甚至偶尔气得想踹门出去散步的人,恰恰是老天爷为你量身定做的呢?他们那些让你恨得牙痒痒的缺陷,会不会本就是一块块正好嵌进你生命缝隙的材料?是上天特意派来那一位,专门负责缝合你灵魂那道你自己都没察觉的破口?
朋友小敏,是个收纳狂魔,家里每样东西都像士兵一样站在该站的位置上,一丝不苟。她的先生?程序员嘛,活在自己的代码世界里,袜子随意卷成球扔在沙发角落是他的常态。小敏说她忍了多少年了,唠叨、划地盘、气得自己关书房生闷气,次数多得数不清。可前阵子她母亲突然病倒,慌乱无措像冰水猛然浇头的时候,是谁在那里?是她先生。他沉默地请好了假,稳稳地开车送她们往返医院,细细致致地料理那些繁杂的入院手续,甚至晚上自己默默把沾着泪痕的纸巾和皱巴巴的缴费单都归拢好,放在了小敏床头那个专门收纳票据的小盒子里。
你知道吗,小敏对我说,声音里有种以前没有的、沉淀下来的东西,那些散落的袜子确实让我冒火,可在那乱糟糟一团的时候,就是他那句别怕,有我呢,和他那种能把一团乱麻慢慢慢慢理顺的性子,真的就像一根锚,把我那条快要被风浪掀翻的小船给稳住了。
说来也怪,我们自己身上那些最顽固、最难改的短板,常常自己视而不见、死活不肯承认。偏偏,它们会被你选择的伴侣以一种让你不太舒服的方式,精准地照出来,或者说,被激发出来。
那个总指责你优柔寡断、拖泥带水的伴侣,是不是恰好戳中了你心底深处害怕选择、害怕承担后果的软肋?让你犹豫不决的,究竟是什么?是贪婪还是恐惧?那个总埋怨你待在家时间太少、不顾家的人,是不是又恰恰照见了你内心深处对于成功那份近乎疯狂、甚至不惜代价的执念?我们究竟在向谁证明自己?
我们总在抱怨伴侣不够体贴、不够智慧、不够支持我们,然而,我们是否曾认真地、专注地、带着理解而非评判地去倾听过对方的需求?他/她那些未曾说出口的、内心深处的渴望是什么?这世界上的倾听,常常只是等待着自己开口说话的机会罢了。
那些让我们在婚姻里、在亲密关系里痛得跳脚、烦得抓狂的矛盾点,那些激烈碰撞的瞬间,会不会正是生命给予双方的一份极其特殊、极其珍贵的成长邀请函?它邀请我们去看见自己内心深处那个一直未被安抚的小孩,邀请我们去审视那些被我们奉为圭臬却可能早已过时的老旧规则,邀请我们去尝试沟通,去学习表达真实的感受而不带指责,去练习接纳那个与我们如此不同、却又与我们命运交织的生命个体。
所以说啊,你身边那个人,或许并非完美的成品,更像是命中注定为你而来的灵魂补丁,专为修补你灵魂地图上那些隐秘的裂痕与缺口而存在。他/她用自己的特质,有时甚至是让你头疼的特质,填补着你生命的缝隙,也打磨着你性格的棱角。这相遇并非偶然的巧合,更像是一次精心设计的碰撞与缝合,两个带着缺口的人,在生命的行进中不断摩擦、调试,直至听见那声彼此契合的咔嗒轻响。
婚姻里最温情的景象,往往不是完美的契合,而是两块形状各异的灵魂碎片,在生活的风雨中,最终拼凑出彼此圆满的缺口。
岁月流转,当我们终于看清那个总惹我们烦恼的人,原来他/她那些所谓的毛病,恰恰是照亮我们自己灵魂暗角的微光。他/她笨拙地、固执地,用自己的方式,填补着我们缺失的那一角。这难道不是生命给予的一份最不同、最深沉的礼物?
那份礼物,不是完美无缺的雕像,而是恰好被精心设计来拥抱你形状的、不同的馈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