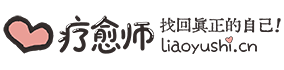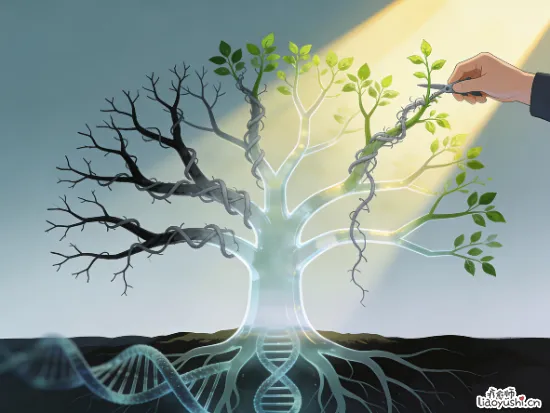那天医生说我得了重度抑郁和焦虑的时候,我其实……好像早就知道了。就是那种,你心里一直有个声音在喊我不对劲,但没人听见,连你自己都想假装听不见。确诊那天,我攥着病历在医院走廊站了好久,纸上的16岁和重度两个词挨在一起,刺得眼睛疼。
原来身体真的会先于心死掉。早晨闹钟响的时候,我的胳膊沉得抬不起来。不是没睡醒,是……是整个人被灌了铅。我妈在门外吼再不起迟到了,可我的脑子像卡住的齿轮,转不动,连掀开被子的力气都被抽干了。手机屏幕亮着,十几条未读消息,但我连点开的欲望都没有。那些红点像针一样扎过来,我担心别人在想什么。
我敢打赌,那个人讨厌我,真的,真的,在我的脑海里,我永远都赢不了。后来才知道,这叫认知功能瘫痪:注意力碎得像玻璃渣,背三天的单词第二天全忘光,课本上的字全是乱码。

夜里才是真正的战场。黑暗放大了所有声音,心跳声、空调声、脑子里循环播放的你不行。我爸总说你就是想太多,可那些念头像藤蔓缠住气管,爷爷葬礼上没哭的我是不是冷血?妈妈去世前最后一句说的什么?数学考砸了人生就完了吗?当我一个人的时候,这种感觉最强烈。独自一人的夜晚真的很难熬。最可怕的是,连眼泪都流不出来,胸口堵着一块水泥,喘气都带着血腥味。
我试过求救的。在作文里写希望变成一朵凋零的花,老师红笔批注修辞不当;和同桌说活着没意思,她笑嘻嘻回凡尔赛是吧你年级前十。后来我学会了笑,咧着嘴,肌肉僵硬得像戴了石膏面具。直到有天划破手臂,血珠渗出来的时候,竟然感到一丝轻松。原来疼痛可以兑换成片刻的清醒。
转折是从一句你需要帮助开始的。
不是振作点也不是别矫情,是我的新心理老师说的。她告诉我,14.8%的青少年正卡在同样的裂缝里,西部和农村的孩子更艰难,有些地方三成留守少年活在抑郁阴影下。数据让我第一次觉得:原来我不算怪物。
治疗像剥洋葱。CBT(认知行为疗法)教我抓出脑子里那群撒谎的小人,比如考不上985人生就完了是灾难化思维,爸妈离婚是我的错是过度归咎。每拆穿一个谎言,就给自己盖个勇气徽章。药物也来了,小小白药片,吃下去手抖、反胃,但两周后某天早晨……我居然闻到了煎蛋的香气。医生说SSRIs类药物要在监护下用,有人吃了会心悸,有人会依赖,但我这条命,那时候本来就是捡回来的。
很大的雷其实是家庭引爆的。
我妈看到诊断书时哭到抽搐:妈妈怎么会把你养成这样?
我爸闷头抽烟,突然说:爹带你逃学去青海看盐湖。
他们开始学习倾听,我抱怨同学冷暴力时,妈妈没再吼人家为啥只针对你,而是握紧我的手;
我瘫在床上拒绝吃饭时,爸爸端来一碗小米粥,上面漂着撕碎的紫菜,像极了我小学喜欢吃的味道。
重建生活是碎玻璃里挑糖渣。
心理老师逼我每天找三个微亮时刻:便利店阿姨多送了一颗关东煮,数学题突然解出第二步,云朵形状像咧嘴笑的狗。后来糖渣变多了,在4D Recovery中心(为康复期青少年建的社区)第一次主动和人拼乐高;跟着APP跳健身操到满头大汗;甚至注册了线上课程重学落下的高一物理。运动分泌的内啡肽比药更甜,虽然开头跑十分钟就肺疼。
现在偶尔还会坠回黑洞。但包里总塞着急救清单:闻狗狗肚皮的触感,单曲循环《Viva La Vida》,给心理援助热线发句今天有点难。
我仍然会感到焦虑和抑郁,但情况正在好转。今天是新的一天,明天也将是新的一天。
昨天路过学校围墙,紫藤花开疯了。我摸着左腕那道淡白的疤,对自己说:你看,连伤口都能长成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