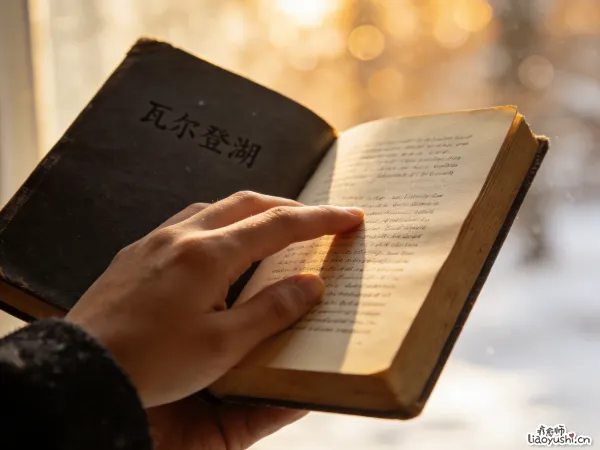地铁玻璃映着我那张紧绷的脸,眉头锁死,嘴角下垂,眼神茫然地盯着飞速倒退的广告牌光影,却什么也没看进去。心里搅着一团乱麻似的焦虑:方才那个项目方案是否还能更完善?老板最后那句话是不是另有所指?下周的房租,还有那似乎永远慢半拍的职业上升通道……每件事都沉甸甸压在心头,仿佛永远没个头。
焦虑这东西,真像缠人的野草。我们个个顶着它奔波,有人被它逼得脚步踉跄,有人被它压得腰背佝偻。那份沉甸甸的重量,你是否也觉得甩不掉?
我后来才琢磨透,那份沉重感的真正源头,其实是我们自己攥得死死的,那些名为执念的顽石,被我们当成了宝贝,死死箍在怀里。
执念是个狡猾的东西。它有时披着追求卓越的华服,有时又假扮成生活保障的务实模样。比如我那位老朋友陈亮,他脑子里就刻着一条执念:必须挤进最顶流那几家大公司,捧着众人艳羡的金饭碗才叫安稳。为此他拼尽心血,几乎把所有的力气都砸进那点事情里。
结果呢?非但没能挤进顶流行列,反而在一次大规模裁员中丢了原来那份其实也不错的饭碗。失落感几乎将他淹没,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昏天黑地,好像世界真的塌了。
说来也巧,人在绝境边缘,有时反而会摸到一线微光。那阵子他终于肯松开那只死死攥着金饭碗的手,一咬牙,拿着积蓄和赔偿金,跟几个以前被他嗤之以鼻的搞小作坊的朋友合作做起了一个小小的文创工作室。工作琐碎又辛苦,充满了不确定,可奇怪的是,他脸上那份被焦虑啃噬了多年的僵硬,竟一天天松动了。他跟我坦言:那天夜里,他盯着电脑屏幕上简陋却凝聚心血的初稿,心里忽然掠过一缕久违的轻盈感,仿佛肩上那无形的沉重枷锁,咔哒一声松开了一条缝隙。
这缝隙,竟成了他真正喘息的开始。
我们对很好的执着迷恋,往往源于一种深刻的恐惧,恐惧被落下,恐惧不够好,恐惧被人轻看。这种恐惧,把无数个应该和必须夯进骨头缝里,沉得要命。
我自己尝过这种苦头。有段时间,我像患了强迫症,事无巨细都要追求完美:报告每个字词必须精准无误,房间要一尘不染。甚至给朋友发消息,都要反复编辑到词句完美才敢发送。那状态真是煎熬,真的睡不着,仿佛总有个严厉的声音在脑后尖叫:不够!这还不够!
直到那个周末下午,在附近小公园里,我被一群孩子吸引。他们在雨后泥泞的地上追逐打滚,衣服沾满泥点,小脸笑得像盛开的花。那份浑然天成的、不计较后果的投入和快乐,像一道光劈开了我自我捆绑的牢笼。那些完美无瑕的念头,难道不就是我自己亲手捏造的沉重枷锁?
皮球拍得再用力,终究要落回地面;积雨云再浓密,终有消散之时。自然万物,本就不屑于执着于某一种固定姿态而耗尽生命。蒲公英轻盈,才借风力把种子播撒远方;竹子中空,才在狂风中摇曳而不折腰。想来,我们那点自以为是的执念,无非是赋予某种暂时的、有限的状态以过于庞大的意义。
松手,有时竟比握紧需要千万倍的勇气。那是对未知荒野的臣服,更是对生命本身流淌不息的本质的深沉信任。
我自己在试图松开对完美掌控的执念时,那种感觉像笨拙地学步:刻意允许报告里留个无伤大雅的小瑕疵;聚会时主动讲个有点冷的笑话而不忙着懊悔;房间稍乱了点,也学着宽容自己。起初真是别扭极了,甚至恐慌,仿佛松开的不是执念,而是自己岌岌可危的立足之地。

然而渐渐地,一些奇妙的变化开始无声地发生。那份如影随形、勒紧五脏六腑的焦虑感,竟像被风拂动的雾气,一点点变得稀薄了。它还在,却不再能轻易窒息我。甚至某个黄昏,当我无意间抬头看见窗框切割出的天空晚霞时,一种久违的纯粹观看的宁静,竟无声息地涌满心间,仿佛身体里积累的厚厚尘埃,终于被一阵清凉的风吹散了表层。
这过程缓慢如抽丝,某些日子,旧有的焦虑惯性仍会裹挟着我向前奔突。但心中已明了方向:握拳越紧,指缝间渗出的焦虑沙砾反而越多;松开掌心,反而天地开阔,连呼吸都畅快几分。
公园里孩子们欢笑的场景常在我脑海里回放:他们投入玩泥巴的那份天真专注,毫无负担,恰是生命最本真的状态。那份自由自在的专注,本身不就是一种轻盈的飞翔?
如果焦虑是那些漫天飘荡的蒲公英种子,我们偏要死死攥紧拳头,妄想牢牢抓住所有,结果呢?种子在掌心闷死,只剩枯萎的绝望;摊开手掌,却能目睹它们轻盈起飞,带着微小却真实的生命力融入广阔天地。
松开执念的手,那份沉重便失了根基。焦虑如同离枝的枯叶,因失去了紧紧抓握的力量,终将飘落于尘埃,不再遮蔽我们仰望的天空。
原来所谓拥有,未必是紧攥;那最牢固的安宁,恰始于松开掌心的一瞬明了:万物皆流,我们所能做的,不过是顺流漂浮,观看两岸风景,在放手中领受宇宙深处的温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