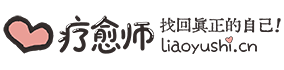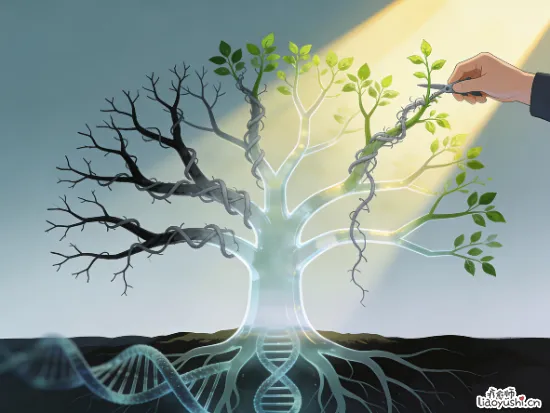医生在诊断书上写下「重度抑郁」这几个字的时候,我心里其实一点波澜都没有。哦,原来是这样。感觉就像一个早就知道自己得了绝症的人,终于拿到了那张确诊单。没什么好惊讶的。
那段时间,我的世界是灰色的。不是文学修辞上的灰色,是物理意义上的。食物没有味道,阳光没有温度,别人的笑声像噪音。每天最艰巨的任务,就是从床上爬起来。被子有几千斤重,身体像被灌满了铅。活着这件事,成了一份没有任何报酬、却必须硬着头皮去做的苦差。
我去看过很多次心理咨询。咨询师们都很好,他们会引导我说出童年,说出那些被忽略的感受。我像一个尽职尽责的好学生,努力配合,挖掘自己。我发现,我从小就是个「好孩子」。从不顶嘴,努力学习,懂得察言观色,永远把别人的需求放在自己前面。
同事拜托我做不属于我的工作,我嘴上说着「好的没问题」,心里却在滴血。亲戚让我帮忙办一件很麻烦的事,我明明没时间,却还是满口答应,生怕对方觉得我「不够意思」。朋友在深夜打电话过来倾诉两三个小时的负能量,我困得眼皮都睁不开,却还在温柔地安慰她,因为一个「好朋友」就该这样。
我像一块巨大的海绵,贪婪地吸收着周围所有人的情绪、期待和责任。我以为这是善良。
直到有一天,我的身体先于我的大脑发出了抗议。它用失眠、心悸、无法抑制的哭泣和麻木告诉我:你快要被撑爆。
我成了一个合格的病人。按时吃药,定期复诊。药能让我的情绪稳定在一个低水平线上,不至于坠入深渊,但也仅此而已。我像一个被遥控的机器人,能完成基本的生活指令,但感觉不到任何生命的喜悦。我依然是那个「好人」。即使在我最虚弱的时候,我妈打电话来抱怨家里的琐事,我还是会打起精神安慰她;我依然会因为拒绝了一个不合理的请求而内疚一整天。

我内心的那个「好人」,像一个严苛的狱卒,用「你应该」、「你必须」、「别人会怎么想」这些锁链,把我牢牢捆住。而抑郁,就是我在这座监牢里,无声的绝食抗议。
转机发生在一个非常普通的下午。
那天我正准备下班,一个平时关系还不错的同事,拿着一个巨大的表格找到我,说「帮帮忙,这个数据我实在搞不定了,你最擅长这个。我晚上有约,急着走。」
那一刻,我听见的不是他的请求,而是我身体里一个声音在尖叫。一种混杂着疲惫、愤怒和厌倦的情绪,像火山一样,冲到了我的喉咙口。
在过去无数个类似的情景里,我会压下这股情绪,然后微笑着说「好啊,放这儿吧」。但那天,我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看着他,非常平静地说:「不行,我也要下班了。」
空气凝固了三秒钟。
我能看到他脸上的惊讶和一丝不悦。我的心脏在胸腔里疯狂跳动,手心全是冷汗。我脑子里那个狱卒在大喊:你怎么能这样!他会觉得你很自私!你们以后还怎么相处!
他愣了一下,有点尴尬地说了句「哦,好吧,那我再想想办法」,然后就走开了。
就这么结束了。
我坐在座位上,后背全是汗。我预想中的狂风暴雨没有来。他没有当场指责我,公司也没有因为我拒绝了这件事而开除我。那个下午,太阳照常落下,世界没有因为我的「自私」而毁灭。
但我的内心世界,发生了一场小小的地震。
原来,说「不」,是这种感觉。有点恐惧,但更多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奇异的轻松感。就像一直背着一个很重的登山包,突然卸了下来。
我好像发现了一个秘密。一个关于「做坏人」的秘密。
从那天起,我开始有意识地练习做个「坏人」。
这不是要去伤害别人,而是允许自己「不那么好」。
我给自己列了一个「坏人清单」。清单上的第一条就是:拒绝。
一开始很难。每次拒绝别人,我都像上刑场。我会提前打好腹稿,演练好几遍。当我说出「抱歉,这个我可能帮不了」或者「我现在不太方便」的时候,我依然会感到内疚。但我也逼着自己去观察后续。我发现,99%的情况下,对方只是去找了另一个人,或者自己想了别的办法。我的「拒绝」并没有造成天塌下来的后果。人们其实比我想象的要坚强,他们有能力处理自己的问题。我不是那个救世主。
后来,我把「坏人」行径升级了。我开始表达我的真实想法,即使那可能让别人不悦。
有一次家庭聚会,一个长辈又开始老生常谈地催我结婚,说女孩子年纪大了就没人要了。以前的我,会尴尬地笑着,点头称是,然后回家自己郁闷好几天。那天,我放下筷子,看着她,很认真地说:「我的婚姻状况是我自己的事,我不喜欢别人这样讨论我。」
整个饭桌瞬间安静了。我能感觉到那种无形的压力。但我没有退缩。我只是平静地看着她。几秒钟后,我妈出来打圆场,把话题岔开了。
那顿饭我吃得特别香。我第一次感觉到,我的边界是被我亲手建立起来的。那种感觉,比吃一百颗抗抑郁药都有用。我的身体里好像有一股力量升了起来,它告诉我,我有权利保护自己不被言语侵犯。
这个「坏人」,还学会了表达愤怒。
以前我从不发火。我认为愤怒是一种失控的、不体面的情绪。所有的委屈和不满,都被我转化成内耗,用来攻击自己。我对自己说:一定是我不够好,是我太敏感了。
后来我才明白,愤怒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情绪。它像一个警报器,告诉你「你的边界被侵犯了」。压抑愤怒,等于亲手关掉了自己家里的火警警报。
我记得有一次,因为一件小事,我和当时的伴侣吵了起来。他习惯性地冷暴力,不说话,不回应。以前的我,会陷入巨大的恐慌,会去讨好他,乞求他理我,把所有的错都揽到自己身上。
那天,我看着他那张冷漠的脸,积压了很久的怒火突然就上来了。我没有哭,也没有歇斯底里,我只是非常清晰地告诉他:「你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让我非常愤怒。它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会让我觉得不被尊重。如果你今天还是决定用沉默来应对,那我们就没什么好谈的了。」
说完,我拿起包,自己出门了。
我一个人去看了一场电影。坐在黑暗的影院里,我不是在伤心,而是在回味那种力量感。我表达了我的愤怒,我没有因为它而崩溃。我发现,愤怒原来可以不只是破坏,它也可以是建设性的。它在为我划定一条清晰的底线。
当我开始心安理得地做这些「坏事」——拒绝别人、表达不满、优先照顾自己的感受——奇妙的事情发生了。
我开始睡得着觉了。
我对食物的味道,又开始敏感起来。我会突然很想吃某个巷子口的麻辣烫。
我开始有精力去关注一些以前根本没力气在意的事情。比如阳台上的那盆绿萝长出了新叶子,楼下那只流浪猫今天好像胖了一点。
世界,慢慢地,从灰色变回了彩色。
我把药停了。是在医生的指导下,一点一点减量的。最后一次去复诊,医生看着我的状态,笑着说:「你好像变了个人。」
是啊,我变成了那个我曾经最害怕成为的「坏人」。
这个「坏人」,会因为不想社交而推掉周末的聚会,宁愿自己在家看一整天书。 这个「坏人」,会在别人提出不合理的要求时,微笑着说「不」。 这个「坏人」,会在感到被冒犯时,直接说出「我不喜欢你这样说」。 这个「坏-人」,会把自己的需求和感受,放在价值排序的第一位。
当然,这个过程也让我失去了一些东西。一些习惯了我「有求必应」的朋友,慢慢疏远了。一些习惯了我「懂事顺从」的亲戚,会觉得我「变了,变得不好相处了」。
一开始我也会难过。但后来我想明白了,那些因为我不再无条件付出而离开的人,他们爱的,或许从来都不是真实的我,而是那个能给他们提供方便和情绪价值的「工具人」。
而留下来的人,是那些真正尊重我、能够和我平等交流的人。我的朋友变少了,但质量却高了很多。
我没有变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坏人。我依然善良,依然愿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别人。但这份善良,是有边界的,是有底线的。它首先要确保,我自己是舒展的、快乐的。
我治愈我的,不是药物,不是心理咨询,而是那个被我重新找回来的,敢于说「不」、敢于表达愤怒、敢于「自私」的自己。
我亲手拆掉了那个关押自己的监牢。我允许自己,不再做一个完美的好人。
我终于,自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