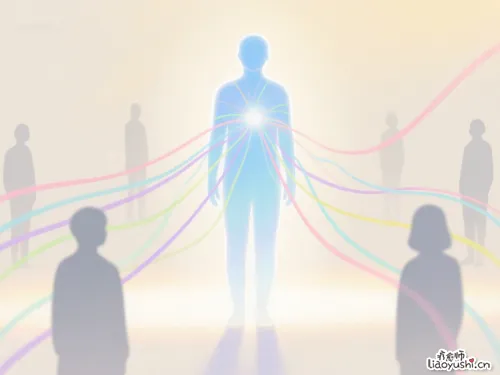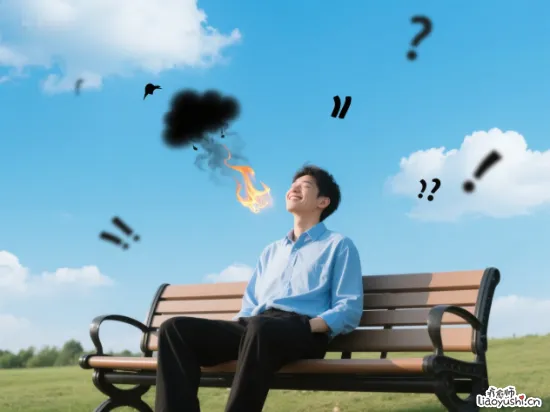上周三,我加班到快凌晨一点。项目卡在死胡同里,进度条像被冻结了,屏幕的光刺得眼睛生疼。脑子嗡嗡作响,像有一群愤怒的蜜蜂在里面横冲直撞。肩膀紧绷得发硬,胃里像塞了一团冰冷的石头,沉甸甸地往下坠。那一刻我清晰地感觉到,愤怒和焦虑像两股滚烫的岩浆,在我身体里左冲右突,寻找着爆发的出口。我死死盯着屏幕,手指悬在键盘上,却一个字也打不出来。想砸点什么?想吼出来?又或者干脆瘫在椅子上放弃?这些念头轮番轰炸。但理智告诉我,不行,得做完。这种撕裂感,太熟悉了,也太折磨人了。真的,那种感觉,真的糟透了。
就在我感觉自己快要被这股情绪彻底吞噬的时候,一个有点模糊的念头,像水底的泡泡一样,突然冒了上来。嗯…是那个…圣多纳法?对,好像叫圣多纳释放法(Sedona Method)。很久以前听一个朋友提过一嘴,说是能快速处理情绪。当时觉得,情绪这东西,还能怎么处理?不都是要么压下去,要么爆发出来吗?或者熬到它自己消失?
朋友当时说得很简单:就是问自己几个问题,情绪就能松动了。
我当时听完也就笑笑,没太当回事。那天晚上,鬼使神差地,那几句话就从记忆的角落里溜了出来。反正死马当活马医,试试呗,总比憋着强。
我深吸了一口气,靠在椅背上,闭上干涩的眼睛。试着去感受身体里那股汹涌的愤怒和焦虑,不是抗拒它,也不是分析它为什么存在,只是去承认:好吧,愤怒在这儿呢,焦虑也在这儿呢,像两个不受欢迎的客人赖着不走。
然后,我在心里,试着对自己提出了第一个问题:现在,我能允许这种感觉存在吗?
这个念头一出来,我下意识地就想抗拒,废话,当然不想允许!它让我这么难受!但很奇怪,当我不再本能地推开它,只是去观察这个不想允许的念头时,身体里那种紧绷的对抗感,好像… 松动了一点点?就像紧紧攥着的拳头,无意识地松开了一丝缝隙。

紧接着,第二个问题自然而然地浮现:那么,我能欢迎这种感觉吗?
欢迎?开什么玩笑!我当时差点被这个念头气笑了。欢迎这股想让我砸电脑的愤怒?欢迎这快把我胃都揪成一团的焦虑?怎么可能!但神奇的是,就在我清晰地意识到不!我绝不欢迎!的那一刻,我反而… 笑了出来。不是开心的笑,是一种有点荒谬的、自嘲的笑。就在这绝不欢迎的念头清晰浮现的瞬间,胸口那块压着的大石头,好像真的被挪开了一丁点,呼吸似乎顺畅了一点点。那种被情绪完全劫持的感觉,稍微淡了一点。
然后,第三个问题来了:如果可以选择,我愿意放手吗?
放手?让这些难受的感觉走掉?这还用问?当然愿意!几乎是立刻的答案。就在心里回答愿意的那一瞬间,我感觉到身体深处,仿佛有一声轻微的、几乎听不见的咔哒轻响。像是什么东西松开了卡扣。那团一直在燃烧、让我坐立不安的愤怒,那股让我胃部痉挛的焦虑,它们并没有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但奇妙的是,它们好像… 不再死死地缠着我了。它们还在那里,但像从粘稠的胶水变成了流动的水,不再死死地吸附着我的每一个细胞。刚才那种被情绪完全淹没、无法思考、无法动弹的窒息感,大大地减弱了。头脑里那嗡嗡的噪音也平息了不少,变得清晰了一些。我居然能重新把注意力拉回屏幕上,开始思考那个卡住的技术点。
这第一次尝试的经历,说实话,有点颠覆我的认知。原来处理情绪,真的可以不用硬扛,不用讲道理说服自己,甚至不用深呼吸十次(虽然深呼吸也有用),更不用等到它自然消散,那个过程往往太漫长,煎熬得很。圣多纳法,它更像什么呢?嗯… 像给你的情绪按了一个暂停键,或者一个松动键。它不试图消灭情绪,而是通过那几个简单得甚至有点傻的问题,让你和情绪之间拉开一点点空间。
就是这点空间,让你有了喘息的机会,让你从被情绪完全控制的状态里稍稍抽离出来一点,重新拿回一点点掌控感。创始人莱斯特·利文森(Lester Levenson)当年据说就是从自己濒死的体验和深刻的痛苦中,摸索出了这套方法。他领悟到,我们所有的不快乐,根源都在于对某种感觉(情绪)的执着和认同。而解脱之道,恰恰在于练习放手的能力,不是压抑,不是转移,是真正的放下、释放。
说起来,这方法的核心,真的就是围绕那三个核心提问展开的。允许(Can I welcome it?)、欢迎(Could I welcome it?) 和 放手(Would I let it go?)。顺序其实不必死板,重要的是在那个情绪涌起的当下,你能记起其中任何一个,然后真诚地向自己发问。允许,是停止对抗的开始,是承认它在这里的事实。欢迎?哦,这个最难,也最容易引发误解。欢迎不是喜欢,不是认同情绪本身,而是欢迎去体验这个情绪的机会,即使它很痛苦。
重点在于觉察到你不欢迎的那个强烈抵抗感,当这份抵抗被清晰地看见时,它反而会松动。放手,则是最终的选择。问自己我愿意放手吗?,答案往往非常清晰,是的,我愿意! 这个选择本身,就蕴含着巨大的力量。整个过程,需要一点点耐心,去感受身体和内在随着提问产生的细微变化,哪怕只有一点点松动,都是有效的。
后来有次,我开车被一个强行加塞的车别了一下,差点蹭上。瞬间一股火噌地就顶到了脑门,心跳加速,握着方向盘的手都捏紧了。就在那股熟悉的路怒要爆发的前一秒,我想起了圣多纳法。我一边盯着前面那辆讨厌的车,一边在脑子里问自己:现在,我能允许这股愤怒在这儿吗?
答案是行吧,它在了,真烦人。然后试着问:我能… 呃… 欢迎一下这愤怒吗?
心里立刻有个声音吼起来:欢迎个屁!这孙子差点害我撞上!
但就在我清晰地听到内心这个咆哮的瞬间,那股顶着的怒气,莫名其妙地就往下掉了一截,胸口也没那么堵了。接着问:我愿意放手吗?
几乎是秒答:愿意!赶紧走!
几秒钟,就几秒钟,刚才还沸腾的怒火,像被戳了个洞的气球,迅速瘪了下去。我甚至能正常地、带点无奈地吐槽了一句:唉,这人开车真够呛。
然后继续专注开车,不再被那股怒气带着跑。这种快速平复的感觉,以前真的不敢想。
我有个朋友,暂且叫她小雅吧。小雅是个容易焦虑的人,尤其在工作汇报前。用她的话说,每次汇报前几天就开始失眠,胃不舒服,脑子里全是灾难化的想象。我跟她分享了圣多纳法。一开始她也是将信将疑,觉得问自己几个问题就能不紧张了?太玄了吧。
但后来一次重要的季度汇报前,她又焦虑得不行,实在没招了,就硬着头皮试了试。她告诉我,当她在汇报前夜,又一次被熟悉的恐慌感淹没时,她躺在床上,心里默默地问:我能允许这害怕存在吗?
她感觉那份紧张稍微被看见了一点,不再像无边的黑暗完全吞噬她。接着问:我能欢迎这害怕吗?
她心里立刻反驳:欢迎?我恨死它了!
但奇怪的是,当她明确意识到自己对焦虑的不欢迎甚至憎恨时,那份焦虑的强度竟然减弱了,身体也没那么僵硬了。最后问自己:我愿意放手吗?
她几乎是带着哭腔在心里喊:当然愿意!快走开!
然后,她感觉紧绷的神经放松了一些,居然迷迷糊糊睡了过去。第二天汇报,虽然还是紧张,但她说那种完全被恐惧控制、大脑一片空白的感觉消失了,至少能比较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了。之后,她开始有意识地用这个方法,虽然焦虑还会来,但她说来得快,走得也快多了,不像以前那样粘着我不放。
圣多纳法最打动我的地方,在于它承认情绪的合理性,同时又提供了一种极其简便的工具去处理它,而不是被它处理。它不要求你变成没有情绪的圣人,只是让你在面对汹涌的情绪浪潮时,能更快地稳住自己,找回内心的锚点。它简单,但绝不肤浅。每一次向自己真诚地发问,都是一次对内在模式的探索和松动。
现在,当我再感觉到烦躁、委屈、压力山大的时候,我有了一个比硬扛、抱怨或暴食更直接的工具。我就停下来几秒钟,问问自己:现在,我能允许这个感觉吗?
或者直接跳到:我愿意放手吗?
就这么一个停顿,一个提问,往往就能让情绪的烈度降下来,让头脑恢复清明。它让我明白,情绪不是主人,我才是。解脱不是遥不可及的彼岸,它就在每一次觉察、每一次允许、每一次选择放手的微小瞬间里累积而成。
生活依然会有无数个像那个加班深夜一样的时刻。但区别在于,当愤怒、焦虑、沮丧这些熟悉的客人再次不请自来时,我不再手足无措地被它们淹没。我知道,只要我愿意停下一秒钟,向自己发出那个简单的提问,允许它?欢迎它?还是放手?,就像在风暴中轻轻转动了一下船舵,虽然风暴还在,但船体已然找到了穿越惊涛的微小角度。
那瞬间的转向,便是光透进来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