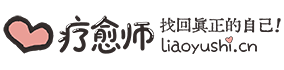我爸的手,是一双很典型的、属于那个年代男人的手。手指粗壮,指甲缝里总是嵌着一些洗不掉的黑色印记,那是机油和铁锈的混合物。他的手能修好家里一切会响、会转的东西,从吱嘎作响的自行车链条,到不肯制冷的冰箱。
但我小时候,最怕的也是这双手。
这双手,会在我考试没考好的时候,把卷子揉成一团,狠狠地砸在桌上。这双手,会在他喝多了酒,和妈妈吵架的时候,挥舞在半空中,带着一股要把整个屋顶掀翻的怒气。
我曾经在日记里写过:我以后,一定不要成为像他一样的人。
后来我长大了,成了一个每天坐在电脑前敲字的文员。我的手很干净,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我几乎不会和人吵架,更不会动手。我以为,我成功地逃离了他的影子。
直到有一天,我新买的键盘坏了一个键。我下意识地把它翻过来,拿出螺丝刀,拧开,检查里面的线路。整个过程,熟练得让我自己都感到陌生。等我把那个键修好,重新敲出字来的时候,我看着自己的手,愣住了。
在那一刻,我透过自己的手,看到了我爸的影子。那双同样在专注地、摆弄着什么东西的手。
一种非常复杂的、混杂着恐惧和一丝暖意的情绪,涌了上来。
我们花了半辈子的时间,想要摆脱父母的影子,却在不经意间,活成了他们的某个侧面。
我们继承了母亲的多愁善感,也继承了她能烧一手好菜的天赋。我们继承了父亲的固执己见,也继承了他在困境中从不言败的坚韧。
这些东西,像刻在基因里的代码,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悄悄运行着。
我有个朋友,他的父母,是那种最本分、最朴实的农民。一辈子没离开过他们那个小县城。他们的人生,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直的愿望,就是儿子能考上大学,在城里找个稳定的工作,娶妻生子。
我这个朋友,从小就跟他们不一样。他不喜欢在田里玩,他喜欢看天上的云。他会用一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他爸妈觉得这孩子「有点傻」。
后来他考上了大学,学了哲学。毕业后,他没去找稳定的工作,他背着一个包,去了大草原,去了很多他父母在电视里都没见过的地方。他写诗,画画,过着一种在他父母看来「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漂泊生活。
有一年过年,我去他家。他爸一边给我倒酒,一边叹气:这孩子,也不知道像谁。我们俩,老实巴交一辈子,怎么就生出这么个『仙人』来。
我朋友就坐在旁边,咧着嘴笑,也不反驳。
他后来私下跟我说:我爱他们。但我知道,我不是他们。我身体里,好像藏着一只鸟,他们是勤劳的鼹鼠,他们希望我也在地下挖洞,但我只想飞。我没办法。
他不是在责怪他的父母。他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

一粒松树的种子,就算掉进了种满白菜的地里,只要它能发芽,它长出来的,依然会是一棵松树。它可能会长得慢一点,可能会因为养分不足而歪歪扭扭。但它不会长成一棵白菜。
它的生命蓝图,在它还是那粒种子的时候,就已经写好了。土壤只能影响它,但不能决定它。
我们总喜欢用原生家庭来解释一切。我之所以敏感,是因为我妈从小就爱唠叨。我之所以缺乏安全感,是因为我爸妈总吵架。我之所以不懂爱,是因为我从小就没得到过足够的爱。
这些解释,有道理。它们解释了我们为什么会这样。
但它们不能用来定义我们只能这样。
认识到土壤的贫瘠,是为了让我们知道,自己需要更努力地去寻找阳光和水,而不是自暴自弃地,就烂在这片地里。
我认识一个女孩。她的母亲,是一个典型的「祥林嫂」。一辈子都在抱怨。抱怨丈夫没本事,抱怨孩子不听话,抱怨邻居占了便宜,抱怨菜市场的菜又涨价了。她的世界,是灰色的。
这个女孩从小就在这种负能量里长大。她一度也变得很爱抱怨。工作不顺心,就抱怨老板是笨蛋。感情出问题,就抱怨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直到有一天,她谈了三年的男朋友,跟她分手。那个男人对她说:我受不了了。和你在一起,我的世界也快下雨了。我感觉自己正在被你拖进一个泥潭。
这句话,像一个耳光,打醒了她。
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哭了三天。三天后,她走出来,做的第一件事,是把她妈的电话拉黑了一个星期。
她说,那一个星期,是她有生以来最清静的一星期。没有抱怨,没有叹气。她第一次发现,原来生活里,除了那些倒霉事,还有很多别的东西。比如,楼下新开的面包店很好闻,路边的小猫很可爱,一部老电影很好看。
她开始有意识地,在自己脑子里安装一个抱怨过滤器。每当「我真倒霉」这种念头冒出来的时候,她就强迫自己,去找一件值得开心的事。哪怕只是「今天早上多睡了十分钟」。
这个过程,非常艰难。像戒D。她说,有好多次,她都忍不住想打电话给朋友,痛骂一顿她的奇葩同事。但她都忍住了。她把那些话,写在纸上,然后撕掉。
她跟我说:我感觉自己像是在和一个看不见的鬼魂搏斗。那个鬼魂,就是我妈的影子,也是过去的我。我不想一辈子都活在抱怨里,活成一个面目可憎的女人。我妈那样过了一辈子,我不想。
几年后,我再见到她。她整个人都在发光。她还在那家公司,但她升职了。她新交了一个男朋友,两人看起来很甜蜜。她跟我讲起她的工作和生活,有困难,有挑战,但你从她嘴里,听不到一句抱怨。
她成功地,把自己从那片贫瘠的土壤里,移栽了出来。她给自己换了土。
我们生命的早期,是被动地被塑造的。父母、家庭、环境,像一个个工匠,在我们这块黏土上,捏出最初的形状。
但我们不是没有生命的黏土。我们是活的。我们有自我意识,有反思能力,有选择的权利。
当有一天,我们照镜子,发现不喜欢镜子里那个人的时候。我们是可以自己动手,把自己重新捏一遍的。
这个过程,会很痛。因为它有时候,意味着要背离你最亲近的人。意味着你要质疑你从小被灌输的一切。意味着你要亲手打碎一部分的自己,再把它重组成新的样子。
这也许是生命中最孤独,也最伟大的一场战斗。
我后来,很少再想起我爸那双挥舞的手了。我更多想起的,是他坐在小板凳上,在昏黄的灯光下,专注地修理一台旧收音机的背影。
我渐渐明白,他不是一个完美的父亲,他只是一个普通人。他有他的局限,他的无能狂怒,他没被治愈过的童年创伤。他把他会的那一点点,好的和坏的,都给了我。
而我,作为一个独立的生命,我的任务,不是去评判他给我的,是好是坏。
我的任务是,把我拿到的这一切,好的,坏的,都当成原材料。然后,用我自己的意志,去建造一个属于我自己的房子。
我不需要成为他。我甚至不需要刻意地「不像他」。
我只需要,成为我自己。
那个修好了键盘,会开心地敲出一行字的我。那个在看到不公时,会愤怒,但会选择用笔,而不是用拳头的我。
我的生命,从他们那里开始。但它的方向,由我决定。它的终点,也只属于我自己。